澎湃思想周报丨数字时代的育儿;凛冬已至好莱坞
技术驱动下的人类生育与数字时代的优生学
当代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的生育过程带来了哪些新的改变?数字和媒介技术如何影响了人类的生育与育儿观念?互联网与科技如何介入当代女性“身为人母”的生命体验之中?“数字时代里的育儿”“数字化育儿时代”等新颖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当下变革与未来图景?这些重要问题正在“科技与育儿”的宽泛背景之下被具体地提出和审视。
《纽约时报》特约评论员阿曼达·赫斯(Amanda Hess)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第二人生:数字时代的育儿》(Second Life: Having a Child in the Digital Age)中结合自身经历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本书被美国《时代周刊》和Lit Hub网站评选为2025年最值得期待的新书之一。《纽约客》近日刊发了特约撰稿人杰西卡·温特(Jessica Winter)关于此书的评论文章《关于未出生的孩子,你究竟应该了解多少?》。《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edium网站、THE CUT杂志等也对本书作者赫斯进行了专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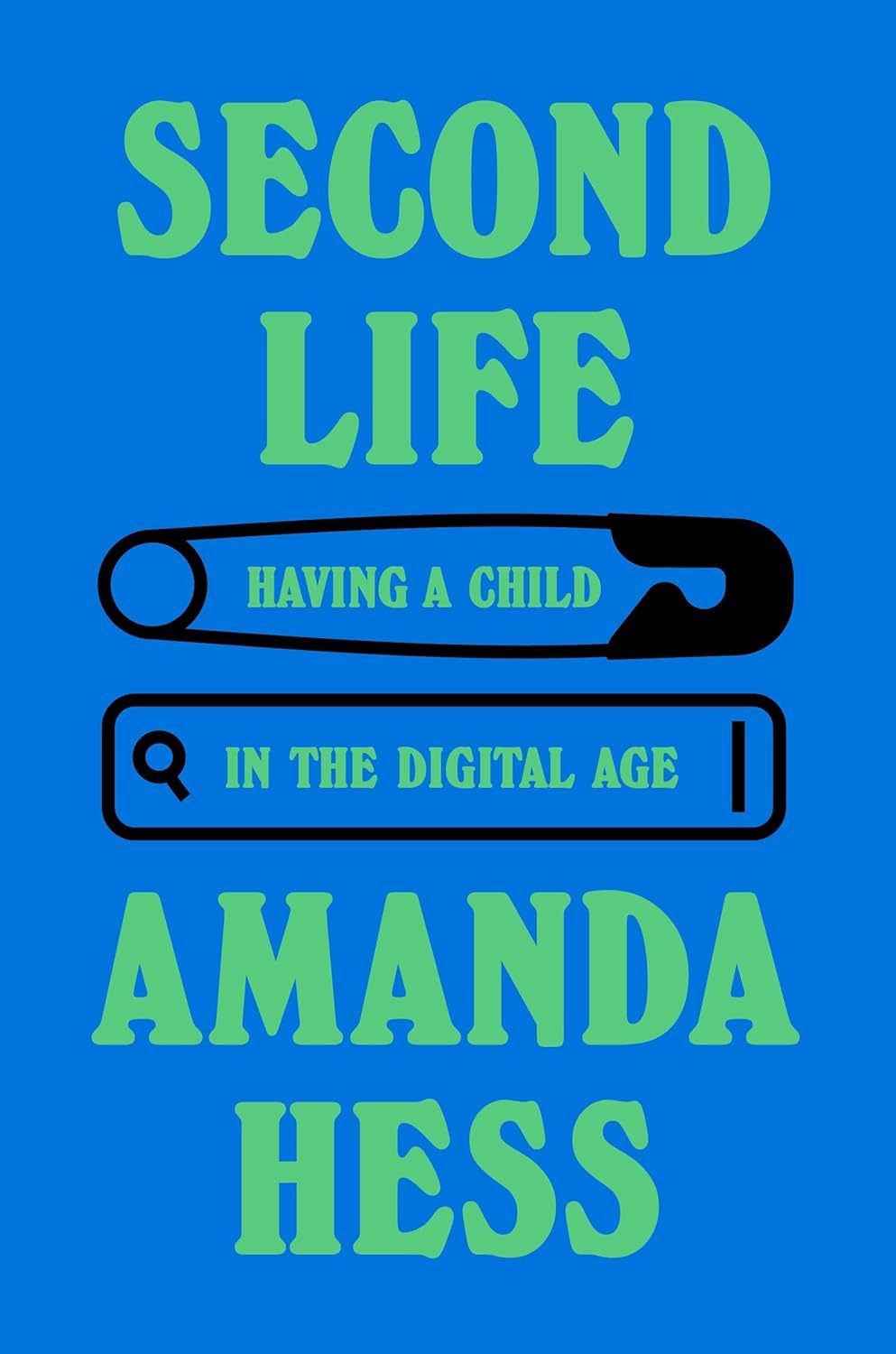
一、屏幕、监控、数字亲密与技术驱动下的“身为人母”
赫斯在《第二人生》中讲述了自己孕育第一个孩子期间发生的故事。2020年,在怀孕第29周的超声波检查中,医生怀疑胎儿患有某种罕见的遗传病,赫斯因此进一步接受了羊膜穿刺术和核磁共振检查——这次检查显示医生的初步诊断是错误的,但疑虑并未就此终止。在第三次检查中,赫斯尚未出生的孩子最终被诊断为患有贝克威斯-维德曼综合征(Beckwith-Wiedemann syndrome)。这是一种基因变异导致的疾病,它会使婴儿患低血糖和某些癌症的风险更高,并且会导致身体过度生长,出现巨舌、脐部突出、内脏器官肥大等异常。由此,赫斯踏上了一段在基因检测领域中摸索前行的生育历程。病例上的相关记录则进一步加剧了她的焦虑。它们包括“高龄产妇”(赫斯当时35岁)、“致畸剂暴露”(她在怀孕六周时服用了一片抗焦虑药物阿普唑仑)以及“孕期焦虑”本身。
在书中,赫斯提到了自己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遇见和与之共存的诸多“屏幕”——从超声波检查的图像到孕期追踪应用程序的界面,从产前基因检测图谱到社交网络上的罕见病脸书群组,从主张自然分娩(freebirth)的网红社交账号到医院里的真人秀,从婴儿监视器到儿童电视。这些“屏幕”深度介入并形塑了她作为孕妇与“母亲”的身份和体验。在赫斯得知胎儿可能患有罕见遗传疾病时,她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机,向互联网寻找答案与对策。“如果我足够聪明、足够迅速地进行搜索,互联网就能拯救我们!”但这些行动并未缓解她的焦虑,反而将她进一步卷入了数字技术为“身为人母”带来的复杂体验中。
在THE CUT杂志的采访中,记者凯瑟琳·莫顿(Kathryn Jezer-Morton)和赫斯谈到了相关应用程序监控女性身体,影响孕妇情感,并对育儿理念产生影响的问题。赫斯在《第二人生》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情景:她在使用孕期追踪应用时曾收到一条通知信息,它说道:“宝宝变得好聪明好协调啊!”——而此时宝宝还在母亲的子宫里呢。
赫斯说道,当女性处于备孕阶段时,这类应用会通过“月经模式”告诉她们:倾听你的身体,了解你的周期,做出明智的选择。而当她们怀孕之后,应用会转变为“孕期模式”并告诉她们:孕育一个最理想的孩子!莫顿认为,这类在婴儿出生之前就不断评估其发育情况并赋予胎儿一些虚假特征的应用程序,有可能会强化某种特定的育儿模式。如赫斯所言,“很多这类技术正在让我们习惯于接受外界对我们身体的监控,并将其视为正常。它们也创造了一种期望,即希望我们的宝宝是‘正常的’,或者事实上是优秀的。”
在此之外,这些“屏幕”也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广告来强化某些“优生”和“优育”观念,完成技术的“个性化”控制。在Medium网站的评论文章《母亲的第二人生:当互联网首先知晓》中,作者帕塔克(Indra Raj Pathak)指出,《第二人生》质疑了“当营销公司掌握着我们最私密的细节时,我们究竟还能对自己的身体有多少控制权。怀孕曾经是一段与家人和亲密朋友分享的私人旅程,如今却与算法、应用程序和广告紧密相连。而这些广告承诺提供‘最佳’的育儿方式。”在他看来,数字时代里,为人父母不再意味着只是从长辈那里汲取智慧,而更多是钻研算法和精准推送的广告,从海量的数据与建议中进行筛选。
譬如,某一品牌的婴儿床承诺可以提供更好的安抚功效,从而将母亲从操心中解放出来。赫斯的婴儿监视器也曾称赞她的儿子“比96%的婴儿睡得更好”。但是,《第二人生》认为这种科技驱动型的育儿方式需要反思。在与莫顿的访谈中赫斯谈到,“我在书中提到的很多技术都是为了抓住这种控制孩子的错觉。”营销人员声称,只要按下正确的按钮,宝宝就会表现得非常好。但孩子不是机器。在她看来,有些公司把安抚婴儿的技术描述得像按一下开关就行一样,这让人感到不安。育儿的重点不是控制孩子,而是与他们建立联系——而这是任何电子产品和监控数据都无法保证的。
简言之,在生育过程中,赫斯对手机、互联网、各种“屏幕”的依赖程度超过了亲友甚至医生。这种数字监控、数字依赖的另一面是一种古怪的亲密感和陪伴感的诞生。在《第二人生》的叙事中,赫斯发现,在她预约医生见面之前,Instagram上的广告就已经先一步地知道了她怀孕的消息。在她尚未做出分享信息的选择之前,互联网已经先于她的“生活世界”知晓了这个重要的秘密。诸如此类的经历展现了科技是如何承诺在人类生育活动中建立新的亲密与联结的,但这也带来了更多的困惑。科技已经全面深入地渗透到女性“身为人母”的私密体验之中,而技术驱动下的育儿方式似乎正在将育儿变成一种“数据劳动”。
二、“扫雪机式育儿”与“硅谷超级宝宝”
在《纽约客》的评论文章中,特约撰稿人温特更为深入地指出了《第二人生》相关联的当代优生学、生殖技术鸿沟与美国中产阶级和硅谷科技新贵的教育观念问题。
文中谈及,近年来,“扫雪机式育儿”(snowplow parenting)概念盛行一时。这一概念用于形容一种富裕且谨慎的育儿方式,“扫雪机式父母”力求在子女人生的每个阶段为他们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多基因胚胎筛查或许是这种“扫雪机式育儿”被推向逻辑极致的体现。温特认为,对于那些愿意花费六位数的学费将孩子送入常春藤盟校幼儿园或接受全面的大学入学咨询的父母而言,如果能够提高未来孩子的智商,他们或许会很乐意在生殖的胚胎阶段进行干预。“这种技术的优势及其高昂的费用对硅谷超级阶层的尼采派(the Nietzschean wing of the Silicon Valley overclass)来说是一个福音,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怀疑是金钱让他们与众不同。而如今,或许他们基因上占优势的后代可以消除所有的疑虑。”
温特写道,许多美国科技公司正在宣扬其筛选最优后代的能力。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 (Sam Altman) 是生物科技公司Genomic Prediction的投资者,该公司提供 “LifeView” 胚胎健康评分测试。这一测试声称可以评估体外受精胚胎的一系列基因疾病,包括患糖尿病、某些癌症或精神分裂症的倾向。Genomic Prediction的联合创始人史蒂芬·许 (Stephen Hsu) 表示,该公司的技术还可以预测智商,但“社会尚未做好准备”。另一家类似的公司Orchid得到了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的联合创始人安妮·沃西基 (Anne Wojcicki) 的支持。Orchid的创始人努尔·西迪基 (Noor Siddiqui) 表示:“胚胎筛查是为了孩子。”
在2024年,The San Francisco Standard网站发表了《硅谷科技精英们想生出超级宝宝。但他们不该如此》一文。文章指出,以“胚胎植入前多基因病遗传学检测”(PGT-P)为代表的最新生育技术,让这些渴望创造“硅谷超级宝宝”的父母们可以像在全食超市购物一样选择婴儿的特征。这类生殖技术在硅谷生育科技热潮中快速发展,服务于科技精英们创造“硅谷超级宝宝”(the Silicon Valley Superbaby)的理想。亿万富翁企业家彼得·泰尔(Peter Thiel)等知名科技企业家投资了Orchid Health、Gattaca Genomics和Genomic Prediction 等初创公司。这些公司承诺告诉准父母如何“降低更多风险”并充分利用“生命的潜力”。他们提供胚胎筛查,以发现心脏病、糖尿病和抑郁症等多基因疾病。Orchid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说道:“不筛查这些疾病简直是疯了!”
此文作者朱莉娅·布朗(Julia Brown)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助理教授,她明确反对了这种“硅谷超级宝宝”的优生学观念。在她看来,关于PGT-P的炒作日益升温,这传递了相反且有害的信息——健康、成功和幸福源于基因、父母的控制和优化。而在温特笔下,对这种优生学的批判更直接地与美国当下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联系了起来。在文中,她以埃隆·马斯克的相关言行为例,指出人造子宫可能性的日益显现(它可以完全消除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正在“为生育产业带来类似DOGE(美国政府效率部)的效率”。
温特认为,“随着科技寡头越来越多地通过不当影响和暴力取代民主国家及其职能和民选代表,硅谷精心策划的生育主义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基因工程,而孩子本身只是抽象概念。”《纽约时报》记者安娜·苏斯曼(Anna Louie Sussman)曾在一系列关于当代生育问题的报道中,总结了硅谷科技界对于育儿与家庭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孩子通常被视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例如阻止人口危机、一个可以优化的项目、一项数据驱动的实验——而不是最终目标本身。”
我们看到,亚马逊网站对《第二人生》一书的推荐语中写道:赫斯记录着自己与数字世界日益升级的关系,并指出科技如何成为令人不安的意识形态、伦理冲突和存在主义问题的入口,同时她也阐明了美国优生学、监控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传统是如何通过这些光鲜亮丽的产品被新一代父母及其子女所利用的。
如温特所言,养育子女并非编程语言,孩子不是一个工程问题,也不是一个需要按照精确规格建造的结构。她提醒我们必须去思考“第二人生”和“超级宝宝”所映射的伦理与社会问题,去思考“这个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使用哪些手段?”以及,“当一个人想要生育孩子时,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凛冬已至好莱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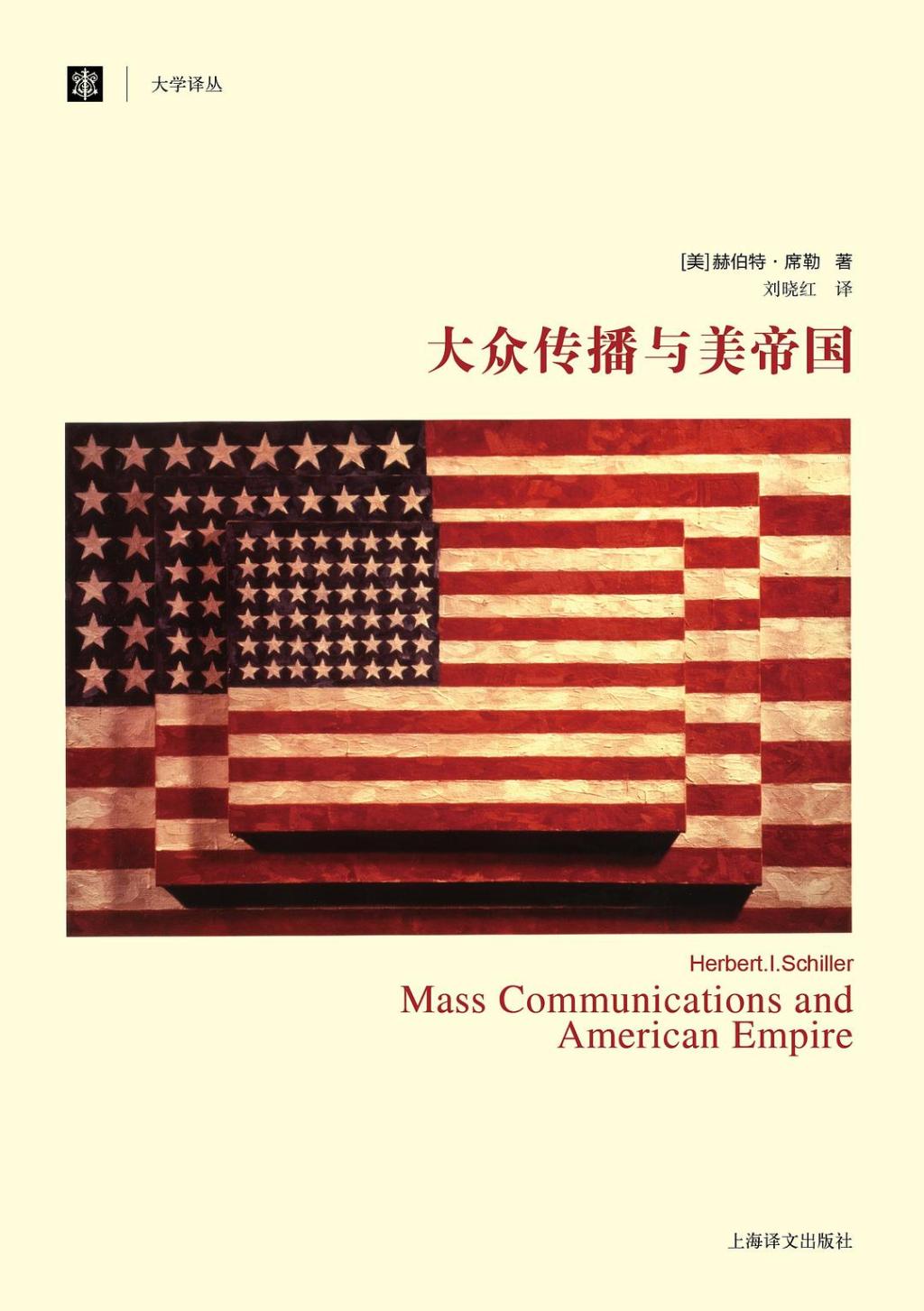
1969年,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首创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他将矛头直指美国,认为美国强大的传媒业对外输出,威胁到了其他国家的本国文化认同。而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攻守易形,伴随着美利坚帝国的全球收缩,曾充当美国文化霸权开路先锋、在全球文化市场势如破竹的好莱坞,正陷入一场深刻的产业危机。
就像美国中西部曾令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工厂一样,南加州的梦工厂也在衰落。除了受新冠疫情冲击的2020年外,2024年是近三十年来洛杉矶外景拍摄最糟糕的一年。到了2025年,衰败的势头有增无减,洛杉矶一季度实地拍摄量、电视剧制作量、电影拍摄量都同比暴跌两成以上。
2025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引述奥蒂斯艺术设计学院近期发布的报告称,好莱坞尚未恢复2023年因编剧和演员罢工导致电影和电视制作停滞而流失的岗位。2024年,娱乐行业的就业岗位数量仍比2022年的峰值低25%。洛杉矶县去年的拍摄天数较2022年减少了42%。报告称:“影视和音像制品行业似乎正在步入一种新的常态,与罢工前的峰值相比,其就业人数和产量均有所下降。”
国际剧院舞台员工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Theatrical Stage Employees)的副总裁小迈克尔·米勒(Michael F. Miller Jr.)表示,在2022 年至2024年这两年期间,大约有18000个全职工作岗位消失。最近对超过 700名剧组成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去年的收入低于预期。娱乐业去年新增了近15000个工作岗位,但这些新增岗位不足以弥补罢工期间流失的所有工作岗位。
报道认为,上述证据越来越多地揭示了好莱坞员工群体面临的危机。专家和从业者均表示,疫情、罢工以及流媒体服务高峰期的终结等因素相互交织,导致好莱坞中产阶级的雇员们陷入了难以维持现状的困境。
在过去两年里,工作量如此之少,以至于编剧、艺术家、布景设计师、摄像师以及其他为影视行业提供支持的众多人员要么另谋职业,要么干脆离开了洛杉矶。一些失业时间长达数月的人在1月份席卷洛杉矶部分地区的大火中失去了家园。好莱坞还面临着来自美国其他州以及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这些地方试图通过提供丰厚的税收优惠来吸引影视产业从加州转移出去。

4月15日,美国娱乐界两大专业报刊之一的《好莱坞报道》发表一篇题为《洛杉矶影视制作业内人士敲响警钟,好莱坞面临重蹈底特律汽车业覆辙的风险》的报道,以底特律为隐喻,直指加州若无法通过政策改革留住产业链,好莱坞可能从全球娱乐中心退化为文化遗址。
4月26日,英国《卫报》发表署名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的评论文章,题为《“感觉空荡荡的”:好莱坞电影和电视制作是否处于死亡螺旋之中?》。文章以一个寂寥的场景开篇:参与制作《角斗士2》《拿破仑》等作品的好莱坞编剧大卫·斯卡帕(David Scarpa)造访好莱坞那些大型制片厂,他深感其中的变化。斯卡帕感慨道:“过去,当你漫步在那些片场时,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忙忙碌碌的。那里就像一个个小城市。而现在你四处走动时,周围常常没有其他人。那种感觉很空旷。在那些片场,你绝对能感受到生机的缺失。”
文章表示,在北美所有电视节目和电影作品中,如今只有五分之一在加州制作。好莱坞电影制作正面临着来自亚特兰大和纽约等本土对手,以及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国际对手的激烈竞争,这些对手都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财政激励措施。而加州的政客们则被指责长期安于现状。
文章认为,虽然特朗普有一个产业振兴的计划,但批评人士表示,该计划于好莱坞而言,与特朗普针对“锈带”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关税政策半斤八两。美国总统任命演员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和乔恩·沃伊特(Jon Voight)为“特别大使”,以拯救当地电影业,三人年龄总和为233岁,此举遭到了广泛质疑。相反,支持者们则把重点放在了加州政府立法出台新的税收激励措施上。
大卫·斯卡帕表示:“州政府和市政府都在为重大财政问题而苦苦挣扎,某种程度上这演变成了‘军备竞赛’:洛杉矶能否与东欧地区相抗衡?我们这里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员,但制片方往往发现自己不得不以最优价格采购服务。如果洛杉矶想要继续保持作为影视制作中心的地位,就必须出台某种形式的税收激励措施。”
文章写道,一个多世纪以来,好莱坞一直是电影业的代名词。南加州阳光明媚的气候使得全年都能进行户外拍摄,而且其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于东部城市。塞西尔·德米尔(Cecil Blount DeMille,好莱坞影业元老级人物)等电影制作人,与派拉蒙和环球影业等公司建立了工作室,确保了演员、导演、音乐家、编剧和技术人员等创作人才的生态系统。好莱坞通过《日落大道》《雨中曲》《玩家》《穆赫兰道》和《爱乐之城》等影片巩固了其自我神话。
加州经济持续繁荣。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的数据,该州的名义GDP达到4.1万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4.02万亿美元,使加州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然而,尽管硅谷的科技巨头们依然蓬勃发展,好莱坞却正面临着一场关乎存亡的危机。据负责处理洛杉矶市及洛杉矶县电影许可证事宜的非营利组织Film LA称,今年第一季度,各类电影制作的产量均较2024年同期有所下降。在此期间,拍摄天数减少了22%,仅有13部电视剧试播集得以制作,这是迄今为止Film LA所观察到的最低数量。与此同时,去年大多数舞台的平均占用率为63%,低于2023年的69%。据《好莱坞报道》报道,音乐配乐舞台预订的拍摄天数从2022年的127天减少到了今年截至目前的11天。
这种萎靡威胁到了那些“幕后”工作人员,比如布景师、电工、木匠、布景装饰师、音响工程师、服装设计师和化妆师,他们之所以来到好莱坞,是因为那里的工作机会多。如果这种吸引力消失殆尽,他们可能会另谋出路,这将导致整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
警示信号随处可见。洛杉矶如今只是全球120个为电影制作提供某种形式激励措施的地区之一。今年2月,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宣布在未来四年每年向墨西哥投资10亿美元用于制作20部电影和电视剧。4月,得克萨斯州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把吸引电影和电视剧制作的资金投入增加一倍多。
文章写道,人们甚至将好莱坞的衰落态势与底特律相提并论。后者曾是“汽车之城”,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困境,它从美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沦为了最动荡不安的城市之一。工厂纷纷倒闭,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流失,人口锐减,最终这座城市宣告破产。
Film LA综合传播业务副总裁菲利普·索科洛斯基(Philip Sokoloski)表示:“我认为我们尚未走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但底特律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说明为时未晚却无所作为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对于加州以及大洛杉矶地区而言,我们在这个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已有一百年之久。”
“一代又一代的人投入了他们的精力、汗水和梦想来打造这项事业,如今却要让我们承担失败的后果。加州低估了其竞争对手想方设法从好莱坞分得一杯羹的持久力。”
索科洛斯基指出,加州仍是产量领先的地区,但其在该行业的份额已降至历史最低点,仅为20%。“这与大多数人认为的好莱坞在电影行业独占鳌头的情形并不相符。这比例非常小,是我们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小比例,所以当一个地区最出名的业务有四分之三是在别处完成的时候,这个地区将何去何从?”
去年10月,Film LA提出,加州需要大幅扩大其电影和电视税收抵免额度,以保持其竞争力。名为“留在洛杉矶”(Stay in LA)的草根运动正在推动相关行动。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提议将每年拨给加州电影和电视税收抵免项目的资金从3.3亿美元增加一倍多至7.5亿美元。
目前有两份议案正在州议会的委员会中审议。一些政客警告称,这些税收激励措施将意味着企业向财力雄厚的电影公司老板们慷慨让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更重要的是保住加州的就业岗位,并为工人提供与高昂的生活成本相匹配的薪资水平。
演员玛丽·弗林(Mary Flynn)说道:“这是多么的凄凉,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穷人和工薪阶层正在向我们的政府呼吁,为大型电影制片厂提供税收优惠,让它们把工作留在加州,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因为我们无法与亚特兰大竞争,那里的最低工资和其他方面的要求都更低。他们不仅利用了税收优惠,还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
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艰难时期——流媒体热潮的终结、新冠疫情、罢工以及野火灾害——之后,有组织的努力得以付诸行动。玛丽·弗林补充道:“我们已经耗尽了大量资源,即便是演员工会-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SAG-AFTRA)这样的组织内部,仍有视频游戏演员在罢工。”
“我们仍深受其害,所以现在轮到全体领导层兑现他们当初所作的承诺,那就是保护工作机会,并为工人阶级群体发声。在加州州级任上的每一位政客都曾为此作出过承诺,所以现在他们必须兑现承诺。”
在即将重返白宫之前,特朗普曾将好莱坞描述为“一个很棒但又非常棘手的地方”,并宣称吉布森、史泰龙和沃伊特将成为他的“耳目”,帮助将其“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
但弗林本人并未把希望寄托在这三人身上:“我不知道像沃伊特这样的人会怎样来拯救我们整个行业,要知道他其实很久都没认真涉足这个行业了。我非常怀疑他们能否成为我们的救星。我不会把鸡蛋放在这个篮子里。”
事实上,目前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救援行动即将展开,业内消息人士称其进展甚微,甚至可以说“毫无动静”。过去衰败的大都市的幽灵依然挥之不去。去年,商学院教授兼播客主持人斯科特·加洛韦(Scott Galloway)在接受Puck 杂志的马修·贝隆尼(Matthew Belloni)采访时曾表示:“洛杉矶现在的情况要比底特律好得多。”
马修·贝隆尼评论道:“当然,与底特律发生的情况肯定有所不同,底特律的整个制造业都撤离了,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产业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壳。娱乐业将永远与洛杉矶有一些渊源和联系,这是因为这里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比如电影制片厂和经纪公司,并且它们不会考虑把总部迁往纳什维尔或伦敦之类的地方。”
“但他(斯科特·加洛韦)并非毫无道理地认为,娱乐业的核心基层(rank-and-file)中产阶级正在被掏空,就像密歇根州那样。在这里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昂贵,对很多这些艺人来说,找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